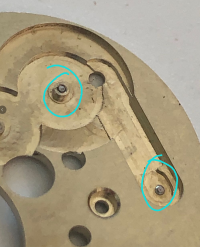在电脑中翻出几年前下载的一篇文章,转帖在这里:
英超联赛“红魔”曼联队的当红前锋鲁尼曾在生日时收到一份特别的礼物——一枚弗兰克·穆勒(Franck Mueller - FM)手表。这是其女朋友的“特别创意”,手表价值1.5万英镑。
FM这最近几年很是红火,作为独立制表大师,他在作品的设计与制作上可谓个性夸张,甚至达到疯狂的地步。一般来说他的招牌是变形后酒桶表壳、色彩纵横的鳄鱼表带。其中的一个系列“疯狂时间”更是让顾客在目瞪口呆之后“疯狂”地接受:1到12点之间的时标被全部打乱,数百年来有序的时间成为一堆混沌——如同在上演诺贝尔得主、耗散结构论者伊里亚·普里高津的《从混沌到有序》,针指也一改昔日温文尔雅的“循序渐近”,疯狂地以跳时的方式指明时刻。
以足球前锋的身份与性格,与FM风格的手表相遇,似乎为天作之合。之所以说这是其女友的“特别创意”,那是因为明星一般会不断地代言一些手表品牌,所戴之表由表商安排,很难按自己的心意去选戴手表。
Andersen时代的另类
独立制表人在表界的出现,意味着与大表商“流行趋势”的对立与互补。各大名牌表商每年推出的手表总会构成大众潮流,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跟着潮流走,所以独立制表人有他们存在的价值与意义,因为他们提供个性。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观点,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是以“创造”为生活的价值,而消费社会则以“消费”作为存在的意义。如何在茫茫人海间找到自己的身份与个性?那就是消费一些个性化的数量极少的产品。但在我看来当大多数人都有追寻个性的时候,“个性”又变成了一种庸俗的潮流。存在主义说存在的本质就是乏味,而我说不管共性还是个性,率性就好。
“独立制表人协会”(AHCI)全名是——“ACADEMIE HORLOGERE DES CREATEURS INDEPENDANTS”字面意为“独立的具有创造力的制表师协会”,它的创立者是Svend Andersen是“疯狂时间”Franck Muelle的老师。Andersen1942年生于丹麦,最早于Padborg的一位表匠处接受制表艺术的启蒙,之后获得皇家丹麦技术学院的制表专门学位。1963年他到瑞士加入Gubelin公司,被指派的工作都是修表之事,他提出许多改善制表技艺的建议,理所当然,都被拒绝了,“我们是聘你来修理,不是来发明的。”部门负责人耸耸肩膀。Andersen急切地想对世人展示他的制表才能,于是别出心裁制造了著名的瓶中钟 (clock in a bottle):先是制造特用的细长制表器具,然后利用这些工具穿过瓶颈,组合出一只怀表般大小的机芯,1969年公开展出,为他赢得了“不可思议的手表制造商”的赞誉,也替他带来一份令人羡幕的Patek Philippe(百达翡丽)复杂机芯部门的聘书。
PP在制表商中作为最高级的独立制表商纵横全球,当然也以个性见称,但Andersen仍然不满意,1979年他创立了自己的工作室,Patek Philippe变成了自己的客户;而1983年收了另一位制表天才Franck Muller担任自己的学徒;接下来就是1985年创立了AHCI。瓶中钟成为Andersen的另一个同义词,可惜的是它不能被戴在腕上。
个性,AHCI追求的正是个性,每年各大表商都会去找到这个团体寻求一些更新的创意,结果又是:个性的普及化又让它成了共性。《圣经》说了,太阳底下无新事。
但我们还是要提一提另一个独立制表人homas Baumagarther,他出生于制表世家,他曾在IWC(万国)表厂工作,也曾向制作机械活动人偶的大师Francois Junod学习过。他的弟弟Felix Baumgarther也是个制表天才,受邀独立制表大师Svend Andersen工作室效力过,成为Svend Andersen的得意门生。而Martin Frei则是个游走于纽约、苏黎世和日内瓦的艺术家、设计师与电影制片人。这三个独立特行的的年轻人加在一起,于一九九五年创立了独立制表人品牌Urwerk。
达达主义在纽约的首领杜象(Marcel Duchamp)曾经质疑过手表在两百年之后的样子,我们当然不知道一百年后手表的样子,但Urwerk创作的手表,似乎在开始回答杜象的疑问了。著名的Ur103 wheite-gold-engravad就是这个独立品牌的作品,这款表几乎没有表盘,至少看上去没有表盘,细长而圆弧形的显示区域被紧紧地压到了表盘底部,毫不起眼,而十二点钟位置的大表冠也被压缩到只剩下一小部份,于是,整块表看上去就是片空空如也的空白,象冬天的大地一样的空白……如果你是一个形式主义者,这款表适合你的个性,不过,你未必能找得到——这就是制表大师人对欲望与个性的戏弄。 |